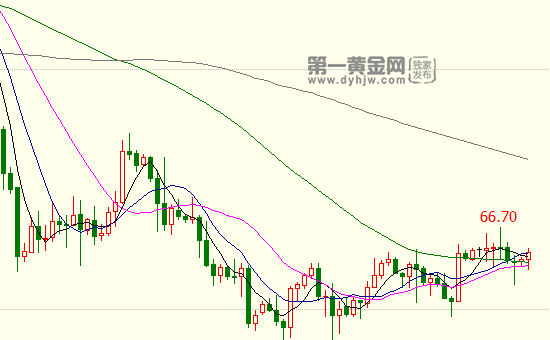一般来说,大家都乐意的事,不一定能成;但大家都不乐意的事,注定不成。
比如公路,大家都乐意,于是成了骄傲,许多路比的新。9月20日,交通运输部发布《2015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》显示:至2015年底,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57.73万公里,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2.35万公里,居世界第一;一级公路9.1万公里,是1984年底的277.3倍;二级公路36.04万公里,是1984年底的19.3倍。
之所以有今日骄傲,从资金上来说,中国公路跨越式发展与“贷款修路,收费还贷”的政策有关,有了这个政策,建路依赖财政投资逐步被银行贷款取代。在中国,银行贷款与财政资金貌似是不同的,前者貌似市场的,但实际上都是政府说了算,行政之手有调动资源的决定性作用。这样,收费公路不只是改变了融资方式,更让地方政府能够更容易、更廉价地筹集到资金来修建公路。特别是,当修建公路不仅迎合了地方政府提升政绩的欲望,还成为高层稳定经济发展的抓手,就使贷款修路成为一个政治正确的行为。
只是,什么事过了就会有麻烦。从2010年以来,中国收费公路的收支从盈余变为负数,2010年尚盈余32.5亿元,之后连年亏损,2011年到2015年收支依次是-323.3亿元、-565.7亿元、-660.5亿元和-1571.1亿元。
为什么会亏得如此夸张?据交通运输部的解释,主要是由四个原因构成:一是收费公路整体规模扩大;二是收费公路剩余期限减少,导致还本付息的压力进一步增加;三是收费标准没有变化,而建设成本却在增加;四是不少省份为了降低财务成本,主动偿还了部分本金,因此导致支出增加。
这不是秘密呀,在公路开建之前,这些是可以测算出来的,但为什么各地政府还拼命上公路?就像计划生育,今日开放二胎,但中国人口增长低迷的窘况已然无法逆转,这些也是可以测算的,而为什么有关方面迟迟不动作?――这不是计算问题,不是会计失职,而是有关方面的利益所在。
公路是什么?它既是一种公共基础设施,也有商业内容,如果在市场中由企业提供,它一定会考虑供求,考虑盈利,必须让规模的扩大有利于边际成本的减少。但如果由政府主导就不一样了,在目前的投融资体系下,收费公路的收益是当任的政绩,而财务压力是由后任来承担的,压力和收益是错配的。而作为百姓,他们并不需要直接承担修路成本,反而有可能从中分得一份劳务收入,因此很少有民众反对公路建设。这样,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、企业、民众,大家都高兴,于是把公路搞成了一个骄傲,骄傲的背后是亏损,是在许多地方过剩,这就要求公路去产能,要求全社会承担损失。
与公路相比,铁路投资更大,运营技术要求更高,更为国家垄断。因此,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,投资的热情都不如公路,资金来源困顿。
按照年初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计划,2016年计划开工项目45个,包括一些客运专线,计划投产新线3200余公里。但在这45个项目中,有些没能按期开工,如原定于一季度开工的安庆到九江铁路,至今未能开工。此外,赤峰至京沈高铁喀左站快速铁路、川南城际铁路等都未开工或推迟了。去年底,国家审计署点名批评了12个铁路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偏低,其中有2个铁路项目投资完成率为0。审计署在公告中提到,据铁总称,投资计划完成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:项目可行性研究批复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以及工程招投标等环节需要较长的周期,个别项目地方资本筹集及银行贷款落实较慢。
资金没备好,谁敢开工?如果后续资金跟不上来就只能停工,停工后人力、物力都耗在那里,投资额会加大。钱呀,都是辛苦搞来的,谁能乱撒呢?铁总负债不断增加,经济又低迷,只有中央政府一家积极,这事不好办。铁路的窘况比公路还甚,比如高铁,除了京沪等少数线路外,其他绝大部分都亏损,西部地区的许多线路都没必要建。
不就是缺钱嘛,千多年前,有位大人物位尊势沉,有得是钱,想和市场扛扛,此人就是石。
1970年代上半期批林批孔,王安石被尊为法家的代表,代表着先进生产力,极具正面形象。然而,王安石除了没什么绯闻,也没因贪腐被调查外,但他最看重的改革,实际上是失败的,他一定此恨绵绵。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?过去的说法是由于保守势力和地主阶级的阻挠所致,这是传统的阶级论。后来各种史料证实,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不仅是地富反坏右,不仅是官僚阶层,还有农民。大家都不高兴,这事就成不了。
当时北宋都城汴京有人口百万,惊得马可波罗合不上嘴。据估量,按购买力而言,宋朝的人均GDP达到520美元,是中国古代历朝中最高的。但王安石还不满足,他想富上加富,当然他是想让国家富,让皇家富,让百姓富,他的品格还是不错的。王安石的手段是官府主导,诸如农田水利法、免役法、市易法、方田均税法、均输法等等都是这路数。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内容是青苗法,“摧兼并、济贫乏”,共同富裕,具体做法是:每年青黄不接时,由官府以低于市场借贷利率向农民贷款,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,秋后农民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官府。
这不是双赢吗?但很不接地气。虽然利息低,但并非农人都需要贷款,而王安石为了证明新政的正确,给地方政府下达了贷款指标,地方官只好硬性层层摊派。偏还有那无良官员,拿着令箭鱼肉百姓,把官府的惠民政策生生变成了强制的官府垄断的高利贷,有的利息竟达原先设定的35倍。
1069年,在首都汴梁延和殿有一场政策辩论,辩论的双方是改革派王安石与保守派司马光,史称“延和殿廷辩”,类似今日林毅夫之辩。王安石认为,中央要实行经济集权;司马光认为,要以农为本藏富于民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保守派和改革派、左派和右派的标签,有时候是乱插的,是不符合实际的。
争辩归争辩,结果是,王安石变法增加了财政收入,数年后,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,“中外府库无不充衍,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”。但是国富了民没富,(,)不高兴了,其中还有东明县一千多农人进京上访,在王安石宅子前闹事。末了,宋神宗不得不下诏停止新法,社会不和谐,一切免谈。
公路照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,虽然政府操持得不讲究,也还过得去;铁路就窘得多,后面不知如何收场;而王安石的青苗法得罪的大多数人,注定没戏。试想,如果今日让王安石主政,举国之力,用行政低利率资金推动铁路、公路五六的跨越式发展,中国会怎样?
 客服热线:
客服热线: